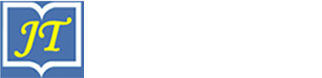唐诗与茶
发布时间:2009年10月29日 09:16 作者:闫永方 浏览: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,尤其是唐代,真是名家辈出,杰作如林;风骨峻爽,情思浓烈,气象雄浑,境界壮阔,韵味悠远;诗体臻于完善艺术达于圆熟,达到了诗国辉煌的巅峰。中国又是一个茶的故乡,茶乃华夏“国饮”,千百年来诗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品茗饮茶,赋诗遣兴,历来为诗家所青睐,咏茶诗自然浩如烟海,于是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——茶文化。茶诗也成了茶文化大观园中一片清馨的奇葩。自唐贞观以来,社会安定,经济繁荣,文化昌盛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这一背景不仅使唐诗的成就达到无可替代的高峰,也有力的促进了茶的种植与传播,出现了“比屋皆饮,举国之饮”的盛况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文人墨客,均以饮茶为高雅之举,而这些文人雅士们在品茶中免不了酬唱应答,交流茶得,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,茶文化就随之产生了。说起茶诗妙品,当首推盛唐。李白有《赠玉泉仙人掌茶》:“尝闻玉泉山,山洞多乳窟。仙鼠白如鸦,倒悬清溪月。茗生此中石,玉泉流不歇。根柯酒芳津,采服润肌骨。”此诗浪漫飘逸,读来若闻氤氲仙气,别有一种神韵。杜甫《重过何氏五首》中第三首描写品茗题诗之乐,也出手不凡:“落日平台上,春风啜茗时。石阑斜点笔,桐叶坐题诗。翡翠鸣衣桁,蜻蜓立钓丝。自今幽兴熟,来往亦无期。”此诗写于汴梁(开封)禹王台,诗人于鸟语花香的春日夕阳之下,边品茗茶香,边凭栏写诗,茶助灵感,诗兴与茶趣融为一体,高雅之至!
一、白居易与茶
把茶大量引入诗坛,使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,从白居易的诗中,我们可以看到茶在文人中地位逐渐上升、转化的过程。
白居易与许多唐早、中期诗人一样,原是十分爱饮酒的,据统计他现存二千八百余首诗中涉及酒的九百多首,而以茶为主题只有八首,叙及茶趣、茶事的有五十多首,可见白居易爱酒不嫌茶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“茶铛酒杓不相离。”这正好说明他茶酒兼好,在他的诗中,茶酒并不争高下。“看风小溘三升酒,寒食深炉一碗茶。”(《自题新昌居止》)又说:“举头中酒后,引手索茶时”(《和杨同州寒食坑会》),前者讲在不同的环境中有时须酒,有时须茶,后者是把茶当作解酒之用。那么究竟白居易为何好茶,一说皇帝下禁酒令,长安酒贵,一说中唐后贾茶兴起,白居易亦多染时尚,都有道理。我们说作为一个大诗人在茶中体会的不仅是物质作用,有艺术家的特别体味。
——白居易的茶激发文思“起尝一碗茶茗,行读一行书”“夜茶一两杓,秋吟三数声”“或饮茶一盏,或吟诗一章”,这些是说茶助文思,茶助诗兴,反过来吟着诗饮茶,茶也更有味道。
——以茶加强修养。白居易生逢乱世,不是一味苦闷的呻吟,而常能既有忧愤又有理智,这一点不是饮茶能够解决的,而饮茶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。“游罢睡一觉,觉来茶一瓯”,“虽被世间笑,终无身外忧”。以茶陶冶性情,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自拔之道是他爱茶的又一用意。所以他不仅饮茶,而且亲自开辟茶园种茶,他在《香炉峰下新置草堂》记载:“药圃茶园是产业,野鹿林鹤是交游。”
——以茶交友。唐代名茶尚不易得,官员文士常相互以茶为赠品,表示友谊。白居易的妻舅杨慕巢、杨虞卿等兄弟常从不同地区给白居易寄来好茶,白居易常与好友共品饮,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茶友很多,如与李绅交谊更深,他在自己的草堂中“趁暖泥茶灶”还说“应须置两榻,一榻待公垂”,公垂指的是李绅,看来偶喝一两杯不过瘾,还要对榻而居,长饮几日。白居易还常赴文人茶宴,中唐以后文人以茶饮交友、会友已是寻常之举了。
——以茶沟通儒、道、释,从中寻求哲理。白居易晚年好与释、道交往,自称“香山居士”,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。白居易还受过称为“八关斋”的戒律仪式。茶在历史上是沟通儒、道、释三家的媒方,儒家以茶修德,道家以茶修心,佛家以茶修性。通过茶静化思想,纯洁灵魂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唐以后三教合流的趋势。
诗僧(茶僧)——皎然
皎然,不是俗人,是唐代的诗僧,也是爱茶入骨的茶僧,是谢灵运第十代孙。他对茶的喜爱和嗜好,近之于痴狂,他在一首诗中说:“丹丘羽人轻玉食,采茶饮之生羽翼。”在日常生活中把饮食看得轻,而多饮茶不仅可以除病祛疾,还能叫人羽化升天。凡是好茶,经皎然饮罢,多半要写诗纪念。他的诗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一诗,赞美的就是浙江嵊县的剡溪茶。“一饮涤昏寐,情来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。”
皎然虽为僧人,他与陆羽的情谊非常深厚,皎然的一首诗《寻陆鸿渐不遇》这样写:“移家虽带郭,野径入桑麻。近种篱边菊,秋来未著花。扣门无犬吠,欲去问西家。报到山中去,归来每日斜。”其是写得清新如话,陆羽的隐士风韵和诗人的仰慕之情跃然纸上。
他俩的情谊又完全是基于对茶事的共同嗜好。他俩在妙喜寺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,二人除了煎茶、品茶、叙茶外,陆羽还在寺旁修了一个亭子,落成恰是癸丑岁,癸卯朔,癸亥日。大书法家颜真卿也恰在这时出使湖州刺史,因此亭子就取名“三癸亭”,由颜真卿题与亭名,皎然写诗“秋意西山多,列岑萦左次。缮亭历三癸,疏趾邻什寺。”陆羽建亭,颜真卿题亭名,皎然写诗,人们传为美谈。一个茶神,一个茶僧,一个大书法家在一起品茗,成了中国茶文化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最后的思考
——儒释道三家与茶文化的渊源
从历史的角度看,道家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人们谈论的最少,但实质上是最久远与深刻的。道家的自然观,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观念的源头。道无所不在,茶道是“自然”大道的一部分,老庄的信徒们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“仙道”,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。玉川子要“乘此清风欲归去”,借茶力而羽化成仙,陶弘景《杂录》与西汉壶居士《食忌》的记载,都与此相关。《茶经·七之事》引述《神异记》的故事,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态度,“自然”的理念,导致道家淡泊超逸的心态,文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,这就确定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。
但从发展角度看,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则应归之于儒家学说。儒家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“以茶可雅志”的人格思想,他们认为饮茶可以自省、可审己,而只有清醒看待自己,才能正确对待他人,由此可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,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,落脚点却在“利仁”,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,所以“中和”思想始终贯穿其中,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,其深层根源仍在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
禅佛在茶的种植、饮茶习俗的推广、茶饮形式的传播和美学境界的提升诸方面,贡献巨大。没有禅宗,很难说中国能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“茶文化”。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,“自古高山出好茶”,历史上许多名茶出自禅林寺院,而禅宗一系列茶礼、茶宴等文化形式建立,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,它对中国茶文化的持续推波助澜,直接造成中国茶文化的兴盛,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对茶文化流传国外,特别是日本,有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。“吃茶去”这一禅林法语所暗藏的丰富禅机,“茶禅一味”的哲理蕴含的深刻涵义,都成为茶文史上的思想精髓。
于是说来,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盛大气象,是由三教合一的文化所造成的。从而体现出“大道”的中国精神,道德境界、艺术境界、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。
——茶文化、酒文化
在传统的饮料中,茶比酒更高雅,茶却不能取代酒在文人情趣中的地位,这不仅因为酒飘逸,茶清爽,还因为酒热闹,茶孤高。茶和酒是一对好朋友,饮茶者不一定喝酒,喝酒者一定饮茶。两者性情差异很大,苏东坡曾说:“佳茗似佳人”。茶确实是个温柔的少女,而酒则是一个侠义的彪形大汉。
中国茶文化的发达,大概和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崇尚悠闲生活有关。鲁迅先生说过:“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是一种‘清福’,不过要享受‘清福’,首先须有功夫,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受……我想,假如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,在喉干欲裂的时候,那么,即使给他龙井芽茶,珠兰窨片,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区别吧。”鲁迅这段话道出了中国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联系。在中国,品茗喝茶,历来是有尊卑雅俗之分的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是一个清高之辈,她对喝茶有几句妙论:一杯曰品,二杯曰解渴,三杯就是驴饮了。苦茶庵主人周作人说:“我的所谓喝茶,却是在喝清茶,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,意未必在止渴,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”在周作人看来,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尘梦。” 这是周作人的“喝茶观”。这种观点是和中国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相一致的。这种观点也是和道家思想的熏陶有关。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教人合乎情理的生活,安贫乐道,宁静清远,不追求奢移豪华,不追逐名利。盛名多景,隐逸多适。于是遁迹山水,过着怡然自得的悠闲生活,钟情于琴棋书画,终日以茶酒为伴,这就造成了中国茶文化、酒文化的发达。
二、一首《茶歌》流芳千古
与白居易交好的卢仝也是一位以善吟“茶诗”而闻名的中唐诗人。他的一曲《茶歌》,即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一诗,历经宋元明清各代,传唱千年不衰,至今茶家诗人仍屡屡吟及。
其诗云:“……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……”卢仝以神乎其神的笔墨,描写了饮茶的感受,茶对于他,不只是口腹之饮,而是给他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。这首诗被誉为“七碗茶歌”,千古流芳。卢仝也因此被人称为“茶仙”、“茶痴”,赢得茶界“亚圣”之誉。《茶歌》的问世对于传播饮茶的好处,使饮茶风气普及民间,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所以人们认为唐朝在茶业上影响最深的三件事:陆羽的《茶经》,卢仝的《茶歌》,赵赞的“茶禁”(对茶征税)。而卢仝的茶歌成为唐以后历代吟唱茶的典故。诗人骚客嗜茶善烹,每每于“卢仝”“玉川子”相比:“我尽安知非卢仝,只恐卢仝未相及”(明·胡交焕),“一瓯瑟瑟散轻蕊,品题谁比玉川子”(清·汪巢林),“何须魏帝一丸药,且尽卢全七碗茶”(宋·苏轼),“不待清风生两腋,清风先向舌端生”(宋·杨万里)。
卢仝祖籍范阳,生于济源,自幼在王屋山下读书成长,很显然他嗜茶如命的习惯的养成,是与他长期以来饮茶分不开的。至于他青少年时期到底喝什么茶,据李菊月考证,推测应是家乡的山茶,卢仝居住的九里沟,路边地头的小叶茶,悬崖石缝中的小石茶,还有王屋山独有的冬凌草,被当地人们称为“红姑娘”的“咽喉茶”等。这些大都属于一两千年生的草本植物,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,济源一代的深山老林里是不是有一种多年生的木本茶树,我不能妄加判断,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济源发生的一件真实事情,似乎能把这种妄断变为可能。当时有个知青叫王长江的,曾在王屋山搞南茶北移,也基本成功了,只是以后政治风云变幻。那位知青后不知何故冤死在狱中,几十年来,没有人再提及此事,只有当年已经成活的几株茶树还在山沟里顽强地生长着。这至少说明,卢仝的家乡大山中,有茶树生长的条件。
卢仝《茶歌》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,就是国外特别在日本的煎茶界将卢仝崇为理想人物,近代日本的煎茶道就是继承了卢仝思想而诞生的。
陆羽——中国茶诗首倡人
唐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,陆羽在考察了各地饮茶习俗并总结了历代制茶经验后,撰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茶书——《茶经》,为人们称为茶道第一人的“茶圣”。
说来也奇,仿佛他天生就与茶有奇缘,陆羽小时候就是孤儿,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主持智积禅师收养,少年时代在寺院度过,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茶结下不解之缘,东汉末期就有人在寺院中种茶。晋朝名僧慧能,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,用亲自烹制的茶招待好友陶渊明话茶吟诗,通宵达旦,被后人传为佳话。到了唐代,僧人们以茶敬佛、献佛,通过信佛,饮茶之风开始由寺院向民间传播。陆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僧人们种茶、制茶、烹茶的经过被他一一记在心间,后来又走出去结交了不少茶友,积累了不少制茶经验,终于完成了《茶经》。一部《茶经》使中国的茶饮走向了世界,使全人类受惠,但是他自己的精神追求却永远是诗。
《茶经》本是讲茶的源流,茶的名称,茶的种植栽培,茶的采制,是教人如何科学种茶的,但是陆羽因为有诗人的气质,把许多茶事活动写的很美,创造出许多诗化的语言。《茶经》在“茶之源”中描述茶的品质时用了“野者上,园者次。阳崖阴林,紫者上,绿者次;笋者上,牙者次;叶卷上,叶舒次。”写得色彩纷呈,可以直接入诗。《茶经》中在描写煮沸的茶沫运动创造了许多新鲜比喻。“其沸如鱼目,微有声,为一沸;缘边如涌泉连珠,为二沸;腾波鼓浪,为三沸。”这些明丽的茶语,为历代诗人所取用。另外像描写早春茶芽,描写茶汤的千万状,都准确传神,他在创立诗化茶饮时,设计了许多新的事象,诸如采茶工具、煮茶的器物、饮茶方法等,也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作为中国茶诗的首倡人,他在《茶经·七之事》里收集了唐以前分散在一些旧诗文中的零星茶诗,如左思的《娇女诗》,张载的《登成都白菟楼》,傅巽的《七诲》,孙楚的《出歌》,王微的《杂诗》,杜毓的《荈赋》等等,这些诗由于陆羽的首次发现,用以作为探讨茶的旁征,以及茶的起源沿革,被世代研究茶的人引用,使尘封了的旧诗,又有了鲜活的生命。
作为茶人,陆羽是幸运的,他留下一部《茶经》光照后人。作为诗人,陆羽是不幸的,一只存有诗作的诗囊不知什么原因丢了。然而不幸中之大幸,他却有两首诗当时就在茶人口中传开,后被唐人笔记小说的作者收在他们的著作里,得以保留下来。清人刻《全唐诗》,将其选录进去,这就是《六羡歌》和《会稽东小山》两首诗。其中《六羡歌》应该说是茶诗中的上乘之作,也是陆羽能够名列诗林的代表作。“不羡黄金罍,不羡白玉杯,不羡朝入省,不羡暮登台,千羡万羡西江水,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这是一首舍弃荣华富贵,把功名利禄看得轻如草灰,志行高洁的好诗,妙在写茶不点一个“茶”字,使诗意更广阔,不受局限,流传也就更广远。陆羽还写过其它一些好茶诗,可惜都散佚茫然,但无论怎样他都可以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茶诗中一个伟大的诗人。
打印本页 关闭